音乐是呼吸,当声音通过你的身体时,你就感到舒适,就像做瑜伽。人的声音汇聚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非常大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听合唱团、交响乐团会让人想哭。音乐的这种连接的力量是神秘的,甚至我们人类现在还不能理解它。
可年轻的时候,我宁愿忍受孤独,也想探索世界的另一面,我想知道另一个地方的人怎么生活。我常在北京的胡同里转悠,好奇地想要进入别人的家,我想看看他们的家是什么样的。
生完孩子之后的那几年,因为暂停了工作,那确实是我最不自信的一段时间。虽然诺一和霓娜都是小天使,我也因为他们的存在成为了“星妈”,但当我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孩子身上时,身边的朋友和外部的环境都在继续向前走。这让我很焦虑。认识刘烨的时候,我是一个一直很敢的女人,现在我变成了一个不敢的女人,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我开始意识到,不工作会让我失去自信。
大学我学的依旧是中文,每年暑假,我都会打工赚钱,然后买机票来中国。20岁那年,我和同学们一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中国背包客之旅。我们先抵达北京,再出发去云南、贵州、广西。我们在乡镇土路中穿梭,我拍下了很多那时的中国,少数民族的热情,他们的习俗、服饰和生活方式深深吸引了我。那趟旅行之后,我回来就申请了去首都师范大学交换半年。
婚后生完孩子那几年,安娜没有工作,感觉自己失去了自信,她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能没有工作,意识到有些压抑着的渴望,“如果不做就会死”。34岁那年,她决定向自己的热爱屈服。
我从小在尼斯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长大,父亲是建筑师、话剧演员,姐姐也是演员。我从小就很喜欢绘画。14岁进高中前要选专业的时候,我天然地就很排斥经济科学,也不想从事任何和商业有关的事。
《温度》展览期间,很多河酒吧时代的老朋友们都来看展,大家被回忆所触动。小河对我说,“这是我们的故事。我们应该做点什么纪念一下。”那时我就快过生日了,我说,要不我生日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展厅做个演出,我也参与,我也唱一唱。
音乐人张玮玮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说“我的音乐审美受到安娜的影响,她给我们带来了世界各地的音乐,让我们感觉自己和世界是同步的”。
我父母有一对教师夫妻朋友,每到暑假他们就会去亚洲玩,拍很多照片。我从小就在投影机上看他们拍的胶片。象形文字丰富的画面感、独特的形状也非常吸引我。印有中文字的纸我都会收藏起来。那时候我就对中国充满了向往:兵马俑、巨石、山水、故宫、麦田……
在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我攥着一个学校地址和电话,对除此之外的消息一无所知,就这样带着50卷胶卷来到了北京。那时我的中文还说得磕磕绊绊,北京刮着大风,大家躲进各自的小家过年,学校里几乎没有人、城市空空荡荡。第三天,我在公共电话亭给爸爸打去电话,崩溃大哭。
到了2017年,我又在北京三影堂举办了摄影展《温度》,这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河酒吧时代的记忆。更多时候,我喜欢使用展览的英文名字“Warm-up”——“热身”。这组照片里,年轻的音乐人在为他们的未来排练,照片外,年轻的摄影师在为她更成熟的作品练习。那是我们所有人“热身”的一段时间,特别美好。
我们的《悲惨世界》排练的时候,每到戏的尾声,当刘烨饰演的冉·阿让对柯赛特讲出那段台词的时候,我都会泪流满面:“柯赛特,你要记住,你的母亲叫芳汀。你现在得到的所有幸福,都是她曾经经受的不幸。”
结束交换、离开北京的前一晚,我在河酒吧唱了一首犹太歌——《金色的耶路撒冷》。那是《辛德勒的名单》的片尾曲。我曾经在这里唱了无数次。我把它送给我的老友,把不舍和忧伤也融进歌里。
中国女人也教会了我太多东西,无论是在贵州还是在北京、上海,中国女性都太厉害了。她们的经验可以给世界各地的女性上一课。她们不脆弱,永远有办法面对、解决生活里的各种困难,她们知道自己其实是很高贵的,从不小看自己。如果可以再选一次,我还是愿意成为女人,因为女性可以拥有很多身份,女性太有意思、太丰富了。
我看到他们在为自己小众的理想而努力,忍受着自己内心的不安、来自外界的不解,坚持创作、探索、特立独行。他们和我一样。我也来自非常普通的家庭,我想要尽快独立,我有自己的艺术理想要去追求,我想靠自己“更上一层楼”。
我在专业目录上浏览,一直往下翻,突然看到“中文”这个选项,忽然之间,很多陌生的画面一下子涌入脑海。我想到书法、毛笔、山水画。说来好笑,中文是那串专业目录里我认为和绘画最相关的专业,就这样,我开始学习中文。
他们来自中国西北,音乐中却有一些西方元素。我从中认出了一些来自几千年前的古老的感受。它纯真又庄严,遥远陌生。我们也要来歌词,尝试去理解他们所唱的内容。
交换接近尾声的那个夏天,我和几位意大利同学一起去了三里屯的河酒吧。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野孩子乐队在台上表演。我被击中了,我们爱上了野孩子的音乐。
2009年,我在北京举办了《北京肖像》个人摄影展,那是那些年我对中国人众生相的一种个人观察,我拍了房产经纪人、记者、卖烤羊肉串的小贩、艺术家、崔健等摇滚歌星,等等面孔。每一张脸上都有他们和首都的独特故事。
其实唱歌是我在14岁的时候就藏在心里的梦想,但是现实中我从来不敢说出来,甚至跟我老公我都不敢说。因为我不自信,我一直没有让自己去做。我就这么憋着,一直憋到34岁,有一天,我突然听到自己的心说,“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我会死”。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非常喜欢这件事。当我终于决定勇敢地去做的时候,发生身边的朋友也很支持我。
千禧年初,安娜背着50个胶卷踏上从法国尼斯来到中国的旅途,那时她20出头,常年在北京的胡同里闲逛,沉醉于云贵高原里陌生的面孔和生活。宁愿忍受孤独,也要探索世界的另一面,那是年轻的艺术家对自己的试炼与承诺。
我们再次见到安娜时,她正和她的“河乐队”从伊犁走到黄山,在云海和怪石间“边走边唱”。2月末,在央华版话剧《悲惨世界》中法巡演启动仪式上,她以戏剧总制作人的身份站在丈夫刘烨身边。刘烨是这次戏剧的男主角,这是他们第一次以合作者的身份站在一起。
那是属于她们的“热身”时代,照片里,年轻的音乐人在为他们的未来排练,照片外,青涩的摄影师在为她的成熟作品练习。他们之外,年轻的北京,它的骨骼也在悄悄地迅猛生长。
去北京这件事,在90年代的法国尼斯是不可思议的。当时整个尼斯几十万人口,去过中国的人可能还不到100个。我们很快轰动了整个小城,还因此上了报纸。那时我除了巴黎以外哪也没去过,甚至没去过意大利。中国对这个小地方来说就是另一个世界,是最远的远方。
我现在回看自己20-25岁的样子,会觉得特别难看,因为不自信,自己把自己藏起来。这和那时候的时代氛围也有关。我16岁起,开始对自己的外貌有所意识,那时候也特别爱美,别人也会说我美,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开始排斥“美”。
1997年,我们高三的中文小班组织了一次去北京的旅行。那时我17岁。一下飞机,我提着行李箱就去了天安门广场,站在毛主席的肖像下,我被震住了。我知道自己站在一个对历史而言特别重要的位置,离我自己的家乡特别远。那些我在杂志、纪录片里看过无数次的中国,现在就在我脚下了。我忽然泪流满面。
90年代,法国女性主义运动迎来第三波浪潮,在那样有些极端的氛围之下,你如果选择做一个美女,就几乎意味着你是一个笨蛋,是脑子空空如也的人。以至于我觉得,如果我美,那我就会笨。我于是把自己的外在尽力隐藏起来,那时我驼背、戴着一个特别大而厚重的眼镜,从不在意自己的发型,尽量穿特别中性、没有亮点的衣服。那是一种很严重的时代偏见,意味着美和聪明不可兼得。
大学毕业后,我得到了一个来中国工作的机会,做法国图片社的摄影记者。阔别半年,再次走进河酒吧时,我已经非常清楚,我就是要用相机记录下这些乐手的这段岁月。摄影就是让自我安静下来,去看别人。我想记录下这些年轻人怎样生活,如何思考,研究他们,就是在研究我自己。
我们都喜欢听世界音乐,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东欧的音乐等等。我也给大家听了很多我在法国时喜欢听的欧洲音乐。即便尼斯和北京,相隔千里,但因为音乐,我们还是跨越了种种阻隔,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了彼此。
这部戏是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的一次特别献礼,由法国国家人民剧院和央华戏剧共同完成。我需要让法国团队和中国团队相互理解,这不只是翻译的问题,而是需要沟通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的人看待同一问题的方式。
我认为自信和果敢的女性是最美的,但我从来不是一个自信的人,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学习自信。自信是一种礼物,但它是生来就不平等的东西。这种不平等并非来自阶级差异,而是家庭氛围。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有一个快乐、阳光、充满能量和鼓励的家庭,那么不管他家物质条件如何,他天然就会是自信的。但如果生来没有得到这些,就需要终身学习。
动因体育篮球馆2024年,中法建交迎来60周年的重要节点。回望来路,两国间良好的交流氛围为无数个体交往创造了条件,而在这场邂逅中,还有更多属于个体的奇遇值得讲述。60年中,无数中法女性于两地文化间往来穿梭,在与未知周旋的过程中,寻找着自己的价值和位置,也逐渐打磨出属于自己的闪耀之美,成为推动中法相向而行的美好力量。三八妇女节之际,我们邀请了7位中法女性,来讲述中法交往中那些属于个体女性的奇遇与闪烁。
2001年夏天结束,我回到法国,正巧那时尼斯正在举办一场13位中国摄影师的联合展览。我也申请展出了我在这次旅行中拍摄的作品。我的展览主题叫“中国,你在动吗?”(China,are you moving?)。
的确很多时候,一代人的幸福是建立在上一代人的承受之上的。我是一名法籍犹太人。2000年初,我曾经参与过一个追寻犹太人在中国的踪迹的摄影项目,以摄影和纪录片为载体走访了哈尔滨、开封和上海,这期间我了解到很多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和上海人之间的温情故事。2018年,央华戏剧引进了一部讲述二战时期犹太民族经历的音乐剧《犹太城》,我担任了女主角。这些经历也让我思考了很多。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6岁,当我在大学和社会上完成了大量的学习,我才对自己的大脑有了一点自信,加上女性的年代终于来了,我终于可以“又美又聪明”了。
直到有一年春节,我真的在胡同里遇到一个大爷,他对我说“你进来,来我们家坐一坐。来我们家过年。” 他给了我一堆吃的喝的,留我在他家看电视,他家墙上贴着很多喜庆的挂画,热热闹闹的。在欧洲,这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原来人可以这样走进陌生人的家里,可以被当作自己人,可以无条件地被欢迎。这种热情深深影响了我,现在的我也是一个好客的人,我喜欢邀请别人来我家。
“我们还活着,我们的孩子可以自己玩耍,也可以和中国的孩子一起玩……虹口人民他们承受着比我们更多的苦难,但他们却对我们的遭遇万分同情,这是一生中最让我觉得神奇的事情。怎么会有人过着比我更艰辛的生活却仍能对我的遭遇感到难过并与我友善?这就是为什么我童年的心灵始终留驻在上海……我充满感激的心永远留在中国并世代留存。友善地对待需要帮助的人是人类的一种胜利。”
我也是那时候认识张玮玮、万晓利和小河的。玮玮总带着一顶鸭舌帽,拉着手风琴,手风琴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乐器,他就像我在巴黎遇到的那些玩音乐的朋友,特别亲切。我渐渐和他们混成了好哥们。
就这样,我和小河、张玮玮、万晓利、郭龙一起,在2018年成立了河乐队,纪念在河酒吧的岁月。我们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安娜和她的朋友们》,也成为一个法国姑娘与中国民谣十余年友谊的见证。
她爱音乐、爱唱歌,也因此误打误撞地闯入中国民谣乌托邦“河酒吧”的时代。无数夜晚,她在那个3平米的小舞台上一遍遍唱起古老的犹太歌,也为这小小一隅,留下无数影像。
就这样,我正式踏上了摄影之路。那是一组极其经典的法国味儿的黑白照片,记录了我在中国的梦幻,也和一些关于巴黎的摄影梦想有关。
如果让我一个人唱歌,我兴趣不大,因为音乐不只是表演,而是人与人的连接,最快乐的永远是跟大家在一起。2021年夏天,河乐队和老狼一起去了新疆伊犁,在草原上唱起自由奔放的流浪之歌,第二年我们又再次相聚在黄山深处,在齐松、怪石和云海之间唱歌。是这些真实的和土地的连接、鲜活的人与人的连接,才让唱歌变得有意义。
孩子四五岁的时候,我开始慢慢恢复工作,最开始我做过一个艺术培训学校,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只能慢慢摸索。直到后来,遇到央华戏剧的创始人王可然,还有很多影视、戏剧行业的朋友,我才慢慢找到自己的热爱和擅长,开始做制作人的工作。我跟王可然合作了很多的戏,《西贡》《犹太成》《雷雨》。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戏剧能走向法国,走向世界舞台。比如孟京辉的戏剧在法国的演出反响很好,但只有一个孟京辉还远远不够。未来,我希望能继续向法国解释中国。可能我自己的角色就在这里,我希望可以做那个位于两者之间的桥梁、那个解释者。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有了解,就会有和平。


 换一换
换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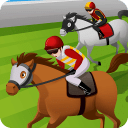


 动因体育篮球馆 v3.7.2官方正式版
动因体育篮球馆 v3.7.2官方正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