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c万象城体育娱乐踏上陕北土地的那一刻,难言兴奋与激动,更多的是忐忑和焦虑。备课工作尚未完成,课时计划临时改动,无数的“第一次”与“不如意”,面临未知深渊的凝视,我试着叩问内心:“我如果做不好怎么办?”
这样的不寻常引起了我的好奇,而我很快便发觉,贴纸乃至文具、书包挂件可能是他们在千篇一律的生活里不多的表达个性的机会,在县中模式下,每天从早上6:10起床号响到晚上10:55熄灯,留给他们自由支配的时间微乎其微,这似乎也解释了在课间短暂的十分钟里,校园内的乒乓球台为何总是人满为患。
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为何而来,又留下什么?是火苗,是种子,是一场破圈,是一次“culture shock”。悄悄地我们走了,正如我们悄悄地来,这座县城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仿佛我们未曾来访。可有些东西,却注定是变了的,一颗名为希望的种子已在孩子们心中种下,虽然听起来很俗套,但在我看来这就是事实,他们对自己和未来的期许被我看在眼里。
7月11日晚,连上三节课后神经还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虽然已经忙了一整天瘫坐在办公室里,心情却久久不能平复,白天的一张张画面在脑海中走马灯般闪过。
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旅程,我奔赴他们的生活而获得治愈,他们向我敞开心扉而获得全新的动力。它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萤烛末光”足以点燃一群孩子希望的火焰,我不再无谓地为自己没有的东西焦虑内耗,而是将自己拥有的倾囊相授,这也许就是受助、自助、助人的精神。我们和靖中的孩子们,两条原本平行的人生轨迹相交,我也衷心希望今后这两条轨迹会逐渐汇聚成双向奔赴的“Y形”,而非萍水相逢的“X形”。
作为高一22班的“副班主任”,在进班之初我并没有找到和他们沟通的最佳方式,相比于有些班自来熟的同学与我们在课下打成一片,我能明显感到22班的孩子们在对远道而来的我们怀有的好奇和热情以外,还有很多的茫然与疏离,或者说他们每天被安排的生活忙碌到根本没时间关注我这个格格不入的“副班主任”。
出乎意料的是,收上来时每张纸都被写得满满当当,问题五花八门,而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词便是“目标”。“怎样树立目标?”“学习动力时有时无怎么办?”“我们每天学得这么苦意义是什么?”一个个问题刺激着我的神经,我该怎么回答这些真诚的孩子?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弱点,也想要做出改变,可一切最终都归结于同一个问题:“what's the point?”
这节课的标题我借用了徐志摩的“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我对他们说:“漫溯”是指在人生道路上不受拘束地自由地探索,但这探索并非是漫无目的的,我们每个人生而不同,选择的道路不同,生活的节奏各异,却有着共同的目标:抵达青草更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后面几天,教学任务逐渐步入正轨,对课堂环境的熟悉也让我更加游刃有余地即兴发挥,以和学生更好的互动教学。6节英语课2节历史课倏忽而逝,课堂上的学生们都极为专注,不时报以热烈的回应,好几个班还强烈要求我给他们加课,本来40分钟的课程愣是上了两个半小时,直到最后我给他们依次签了名、拍了照,这才罢休。于我而言,教学可以说是这次活动中最轻松而自豪的部分了。
这就需要我们做到两点:一是放下执念,给自己松弛感。这些孩子每天实在太忙了,忙到根本没时间和自己对话,被安排久了的结果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哪里谈得什么目标,在意的不过是年级排名、各科成绩这些数字。我建议他们每天把睡前五分钟留给自己,回顾这一天都做了什么,收获了哪些开心的事,多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因为健康的心态是拥有长期动力的前提。
无力感涌上心头。没有目标就没有意义感,也就没有长期坚持的动力。我又想起班主任在初见时嘱咐我的话:“这里的孩子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目标,家里条件不错,觉得以后留在家乡维持现状也挺好,向上的动力不足。”
来支教前家中做教师的长辈就提过:“当老师的情绪价值最好满足。”此言诚不欺我!我觉得自己很适合当老师,至少在来之前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只有当我站上讲台,专注于表达自我,我才会暂时忘记萦绕在我心头的焦虑感,沉浸在独属于我和听众的世界中。
当学生跟随着我的节奏在游戏中领悟英语生僻词的奥秘,在地图上领略到文明演进的历史魅力,看着他们放松肆意的笑,看着他们豁然开朗的笑,看着他们被理解被认可的笑,拿着他们争相递过来要签名的课本,看到他们一笔一画把我讲的内容记下,读着他们写给我的走心小作文,之前的一切艰辛酸楚,此刻都不足为外人道也。
班会课结束后,也快到了分别的日子。合照时我问他们还记得我讲的课吗,他们笑着回答:“当然。”紧接着就听到“舒适圈”、“松弛感”这些字眼,我松了一口气——他们确实听进去了。虽然我不知道多少人会真的有所触动,但我能从他们的眼神中感觉到,变化正在发生……
一是那天还有五分钟上课,我在教学楼外踱步等待,突然教室里一位同学看到了我,开始透过窗户向我挥手,我微笑着回应她,而紧接着是整个班、整层楼、整栋楼,夕阳将教学楼晕染成金黄色,我看到的便是4层楼的学生有的隔着窗户,有的趴在走廊的栏杆上,有的直接从教室里飞奔出来,微笑着在阳光下向我挥手的场景。那一刻似乎全世界都在向我挥手,这样的情景在支教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次,而我和他们中的大部分事实上素不相识。
二是在和老师们寒暄时,我都会提到当地的著名历史遗址统万城,作为历史系的学生对其可谓慕名已久。让我颇受感动的是,老师们的第一反应惊人的一致:“你想去吗?我开车带你去啊!”班主任的工作十分辛苦,早上6点多就要到校盯班,到晚上11点多才能回家,面对素不相识又和学生年龄相仿的我,他们却完全没有老师的架子,更多的是谦虚的“不耻下问”和朋友般的热情邀约。
四是上完课后,我的带教老师和我畅谈许久,她对我的课堂表现很认可,提到我是天津人,她一下来了兴致,和我聊起她的女儿也在天津读书,我看着她眉飞色舞闲话家常,仿佛坐在对面的就是一位家中亲和熟络的长辈。谈到最后,她望着我郑重而感慨地说到:“复旦大学的学生真是不一样啊!”我深受感动,在这里我的一言一行不再代表我个人,而是复旦人的形象,想到这里,我感到诚惶诚恐又与有荣焉、何其幸哉!
中学时代的记忆霎时于眼前复现,恍惚间我看入了神,以为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正要在一天的疲劳后偷得半晌闲暇,享受成年人或不屑一顾或求之不得的小确幸,回过神时,大巴车已经停在了靖边中学的校门口。
靖边中学的门面比我的高中要壮观、宏伟得多,几十米宽的校门、众多高大威严的石柱在这座县城里被衬得格外显眼,这便是我对这所学校的第一印象。
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我们来支教才不是什么下凡的“救世主”,那不过是象牙塔里的大学生自负至极的想法。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只是“闯入”了他们的生活,不过几天便又消失不见,也许老死不相往来。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焦虑难道是因为赋予了这项活动过于“神圣化”的意义?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支教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能留给他们什么?
“既然他们不愿或者说不能向我迈出第一步,那为什么不能是我去奔赴他们的生活呢?”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于是第二天,我开始跟他们一起晨跑、做操,一起听听力、做周练,课间我会不时进班和同学聊聊天,我观察到他们的书桌上贴满了琳琅满目的贴纸,上面都是一些或吐槽或励志的表情包。
想来有些讽刺,我怀揣着“送教下乡”的理想而来,先被治愈的却是我自己。讲台上那一瞬的自信从容对一个习惯于自我否定的人来说,是内耗时的“救命稻草”,而这稻草是靖边中学的人们用真诚与热情赠予我的。
二是走出舒适圈,永不满足于眼前的风景。我给他们分享了一张我和朋友的合照,上面标着每个人的大学去向,还有一张各省高考录取率的排名。我想告诉他们,朋友圈和平台对个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从小学到大学从不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哪怕之一,但也正因如此我结识了许多比我更优秀的同学,也从未丧失学习的动力,因为我看到了我未来努力的方向就在我身边。如果让我给出一个努力学习的理由,我会说“为了站上更高的平台”,因为当你身边围绕着优秀的人,其实动力自然就有了,环境的力量有时胜过千言万语,而你在不知不觉间就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充分融入他们的生活两天后,我给每位同学发了一张便签纸,让他们在上面写下想问我的问题。说实话,当时我很害怕他们会不配合,因为之前我在班里的时候完全没有人来找我问问题,这跟其他班的孩子有很大区别。
一幅幅画面在我脑海里浮现,我看到老师眉头紧锁把我“请”下讲台,我看到孩子们期待的目光渐趋暗淡,我看到自己同学望着失落的我,欲言又止……
我拿着行李走进校园,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学生们好像对我们的突然到来有些懵,纷纷驻足观望。我走在队伍最前面,时不时抬头和学生对视,他们有的回报以礼貌微笑,有的和朋友相视一笑窃窃私语,有的则只是自顾自地向校外走去。
大巴车窗外的喧闹声打断了我无谓的内耗,我看到几个身着校服的学生向我们挥手致意,他们没有背书包,有说有笑地向校外走去,正值晚饭时间,想必是去觅食的。街道上顿时成了蓝白色校服的海洋,他们有的手里拿着书本,嘴里念念有词,边走着时不时还翻书看几眼;有的因为天热将长袖校服系在腰间,手里拿着辣条和同伴分享。
三是在下课时,学生们冲上讲台簇拥着我,对我说:“老师你真绝酒”,“绝酒”是陕北话厉害的意思。我看着他们真诚的脸庞让他们再教我几句陕北方言,他们好像打开了话匣子,侃侃而谈边说边笑,我想这可能是我为数不多的机会去真正融入这座本与我风马牛不相及的城市和这里的人们,而他们似乎也乐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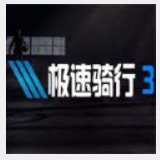

 换一换
换一换
































 awc万象城体育娱乐 v1.5.6官方正式版
awc万象城体育娱乐 v1.5.6官方正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