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村里的人来说,家暴已是司空见惯。我决定到关中某农村利用花馍进行一场反家暴艺术巡展。陕西以面食为主,其中花馍被称为母亲的艺术,而母亲都是和蔼可亲的形象,但“打倒的媳妇,揉到的面”是一个暴力场景,这种反差非常有冲突性。
上大学后,我远离了家乡,爸妈对我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改变。我爸话里话外都有一种孩子翅膀硬了、管不住的感觉。其实有段时间,我非常怨恨我妈,是那种印在身体里、没有办法忘却的恨。直到后来,我开始慢慢理解她:我爸不爱沟通,爷爷重男轻女,我妈跟我爷爷关系不太好,加上她身边没有什么朋友,会觉得孤独无助。我爸是那种典型的理工男,喜欢修车,每天都钻在车里面。
整个讲述过程,于阿姨说话的声音很小,眼神回避,都不怎么敢抬头看我。聊到后面时,她声音哽塞,眼睛湿润。所以,我也没敢深入问具体细节,害怕伤害到她。
此前,我有过驻村经历,跟当地村民比较熟。村子有一个“自乐班”,就是村民自发组织的文娱班子,我通过“自乐班”的成员,宣传自己正在做这个活动。很快,一些人开始报名参加。
前期,我去关中的村庄调研时,问村里的几个阿姨,“打倒的媳妇,揉到的面”具体是什么意思。她们告诉我说:“它的意思是女人就像面一样,打着打着,媳妇就听话了,面揉着揉着,就揉好了。”
我的父母,包括我舅舅他们的婚姻,或多或少伴随着家暴。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你无能为力,但这样的婚姻肯定会影响到小孩。所以,我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
但我没有放弃,我这人比较倔强、好强,就想证明给我妈看。当年联考成绩下来时,我是学校第一名,后来高考是浙江省美术生统考400多名。
我们队伍包括12个敲锣鼓的村民、7个做花馍的阿姨、21个社火表演的叔叔阿姨,加上当时给我们提供场地以及开三轮车的村民,整个队伍大概有六七十人。
一直到这个项目的视频发布后,我才联系到于阿姨的女儿,对方说她一直想记录妈妈的故事,看到我的视频和文字后,很高兴妈妈有这样一个渠道去诉说自己的抗争,她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视频,并对家暴说“不”。
有两位阿姨明确表示,自己遭受过家暴,但没有想过离开丈夫,一方面是丈夫不让她们离开,另一方面,她们也担心离婚后儿子找不到媳妇。
上高中时,我开始变得有些“叛逆”,不想去学校学画画,主要是不喜欢教画画的老师,觉得他教得不好。但我妈坚持让我去学校学。一开始,我爸妈对我进行言语暴力,后来发展到肢体暴力,发现这些都没有用后,我妈直接跪在地上求我去学校。但我坚持说“不去”。
去年,我去村里做前期调研时,阿姨们对我这个外来者比较警惕。一直到去年七月,项目正式执行的当天,花馍老师带着7位阿姨一起捏花馍,老师是临潼人,先自己讲述了她一个朋友被丈夫用砖头磕破了头,之后被送进医院住了两个月的事,才慢慢打开了阿姨们的心扉。
一直到2011年,四个小孩都长大了,于阿姨卸下责任,下定决心跟第二任丈夫离了婚,之后一个人去了西安打工。但不久,对方又托人叫她回去,还说她一个人在外面不好过,回家生活更安稳,于阿姨心一软就回去了。
于阿姨告诉我,她结过两次婚,第一次离婚时还很年轻,当时生了两个女儿。离婚后,她和第一任丈夫各抚养一个女儿。那个年代的农村,女人离异后带着孩子回娘家会遭受排挤。于阿姨后来认识了第二任丈夫,对方当时给予了她精神方面的支持。
我挑选了7条家暴相关的新闻,都是丈夫以各种形式家暴妻子,并利用花馍的形式还原它,即在花馍上捏七个家暴的场景。此外,我又找了村里的七位叔叔和七位阿姨扮演“七对夫妇”,给他们化了“社火”的妆容,社火是陕西、甘肃一种游神的形式。
一开始,我妈觉得我是在作,后来,她带我去了医院检查,诊断结果为重度抑郁。他们不了解抑郁症,对此也并不重视。其后,我断断续续休学了半年。
第一天,我邀请了几位阿姨揉花馍、组装花馍;第二天早上,开始做社火的化妆。我提前租好了衣服,邀请了两个专门给剧团化妆的老师,她们给阿姨们化了“家暴妆”,即脸上带一点淤青、血痕的那种妆容。当天下午五点半,我们开始围着几个村子巡演,一直到天黑。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因爷爷重男轻女,我妈一直对我要求特别高,她望女成凤,希望我能为家里争口气,甚至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了我的身上。
反家暴巡演过程中,村里很多人跑出来看。当时正好是吃饭的点,我记得,一位大爷端着一碗面,急匆匆地跑出来看。到第二个村的村委会门口时,有很多老人小孩,加起来有五六十人围观。当时,一辆三轮车没油了,一辆三轮车爆胎了,场面有点混乱。
我记得其中有一位阿姨说,她婆婆曾跟她说,你生了一个女儿,你女儿丢在关中环线上(注:村边的一条马路)都没人捡。我当时听着心里蛮难受的。
一直到7年后,53岁的于阿姨才再次离开第二任丈夫。我清楚地记得,于阿姨说,她就算是死也要逃出去,那种决绝和怨恨让我很心痛。
“七对夫妇”扮演社火,站在七辆三轮车后面表演家暴场景,每一对“夫妇”还原一个新闻场景,比如丈夫拿刀砍妻子、丈夫拿棍子打妻子、丈夫掐妻子脖子等。
于阿姨记得,离婚不久,前夫突然不愿抚养小女儿了。他对于阿姨说,小女儿跟村里一小孩打架,把对方打伤了,他管不了,希望她能把小女儿也接走。当时还是于阿姨男友的第二任丈夫知道后,立即跟她说,“你把娃接来,我们一起来养。”
我妈脾气暴躁,而且控制欲强。我印象很深,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考得不太好,当时正在补习班做作业,我妈突然冲进教室扇了我一巴掌。
我爸话很少,也不怎么管我。我初中考高中时,成绩比较差。我爸觉得,考不上高中,我去读个职高也蛮好的,但我妈坚持要送我去补习班,她一定要我上大学。
于阿姨要开灯看报纸,丈夫不允许,“啪”的一声把灯关了。于阿姨不愿妥协,又把灯打开,很快又被丈夫关掉,这样来回几次后,丈夫直接动手打了她一顿。
夫妻俩经常因为这样那样的小事而吵架,重组家庭的复杂也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后来,第二任丈夫请人算命,听算命先生说他这辈子要娶三个妻子,于阿姨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便开始对他们的婚姻失去了信心。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正好来大姨妈了,起不来,一直躺着,感觉血从我身体里流了出来,就是动不了。我当时有些抑郁,清晰地听见我爸妈跟我讲话,也很想回应他们,但我就是张不了嘴,像是失去了语言功能。
因为切身的经历,杨桃很早就开始关注家暴。她是西安一所高校实验艺术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读大三时,偶尔听说陕西农村的俗语:打倒的媳妇,揉到的面。意思是,面团越揉越光滑,媳妇越打越温顺。她吃惊于人们对俗语中潜藏的暴力视若无睹。
我后来反思,父母那种不可控的极端情绪,是因为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觉得不安全,觉得失败,所以希望我能按照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生那样成长。
巡演结束后,几位阿姨抓着我的手激动地说:“你是在做好事,让更多的人知道家暴不是一个好事儿。”事后,还有阿姨单独跟我聊遭受家暴的经历。
于阿姨不敢离婚,她说,那个时候农村苦,家里孩子又多,她担心再次离婚的话,自己一个人养不活两个小孩,而且她那时也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
上大学后,我跟我爸妈的关系变缓和了,甚至隔三差五地在线上聊天。有段时间,我妈总跟我吐槽我爸,后来我只要说我爸不好,我妈就会帮我爸说话。他们老了,性格也变温和了。
某一天,我跟一位朋友聊天,谈到网上的一则家暴新闻,对方突然说一些农村对此习以为常,陕西农村流传一句俗语,叫“打倒的媳妇,揉到的面”,我听后特别震惊。
家暴是一个需要被关注的事情,这也是我决定做反家暴展的原因。今年夏天,我把视频发布到网上后,我个人的社交平台,包括网络上的一些跟帖,出现了一个留言互动角,很多人在那里诉说被隐藏起来的伤痛,让它成为了一个情绪宣泄的窗口。
大阳城app下载去年夏天,杨桃在陕西省关中农村举办了一场反家暴的社火巡展,她邀请了村民扮演七对丈夫和妻子,将新闻中家暴的场景还原出来。今年六月,她把相关视频发布到网上后,引起了网络热议。
1995年,于阿姨跟第二任丈夫结婚了。一开始,两人相处还好,于阿姨尽心尽力经营家庭,把丈夫的两个儿子视如己出。但很快,她发现第二任丈夫脾气暴躁,控制欲强。
最开始的几个月,我主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包括跟村里的阿姨们沟通,请花馍老师教阿姨们做花馍等。一直到去年七月中旬,才正式执行项目,花了一共两天时间。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人,之前在西安某大学读实验艺术专业,今年夏天毕业。我们学校的实验艺术专业有一个社会介入的方向,大概意思是以艺术家的身份介入社会现场,用艺术的方式去讲述社会现象。
我小时候比较淘气,那时学画画,不时因偷懒画不完。我记得,有一次画画课结束后,我妈用电瓶车载着我回家,她当时心情也不好,听老师说我没有画完后,很生气,骂了一路,骂着骂着突然直接把我从后座推了下去。幸好当时没有发生严重的后果。


 换一换
换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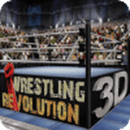


 大阳城app下载 v7.9.5官方正式版
大阳城app下载 v7.9.5官方正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