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外来孕产妇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原先在我们产科最高峰时,4/5都为外来孕产妇,但最近这些年,外来孕产妇降得很明显,有些是为了孩子读书考虑,大家更愿意回老家生了。”伍颖这样感慨。
“作为郊区一家区域医疗中心,我们医院的产科服务功能一定会保留下来,我们同时还服务了周边四个镇。”为稳定产科医生队伍,华敏所在的医院对产科医生的薪酬待遇给予一定倾斜,“不少综合性医院会考虑将妇产科放在一起算绩效,我们医院也是如此,这样一来,产科医生的收入会相对稳定。”
年龄是产科医生转型的最大障碍。45岁的产科医生伍颖也有一番感慨:“如果你还年轻,就还有资本学习新的东西转岗,但年纪大了,上了50岁了,就不会再去考研,转型就很难,或者就只能去做做医疗无关的工作了。”
2024年3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下称《通知》),强调公立医疗机构要承担产科服务兜底责任。根据要求,人口30万以上的县(市、区)原则上至少有2家公立医疗机构能够开展助产服务,人口30万以下的县(市、区)原则上至少有1家;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地区要保障相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具备助产服务能力。
在段涛看来,出生人口的下降原因很复杂,其中一大原因是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在某种意义上说,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成反比例关系。这是一个很难去打破的魔咒,这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汪栗在上海一家区级综合性医院工作,见证了医院整个产科的发展历程。“从过去的‘一床难求’逐渐变得‘门可罗雀’,再到彻底关停,部分产科医生去了行政部门,另一些去了院感科。产科一关,妇科也跟着萎缩。”
纵观全国,医院产科关闭也不再是个例。一年来,浙江、广州、福建等地多个省份的医院暂停或取消分娩服务,仅媒体报道的就超过了10家,目前大多仍集中在中小型医院。
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当下,产科正步入“寒冬”。2024年2月末,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段涛教授发文呼吁“救救产科”,引起诸多产科医生共鸣,也道出这一群体的隐忧:产科关闭后,我们转行做什么?
“生的人少了,产妇更愿意跑去大医院建卡,毕竟大医院对疑难危重情况的处理更有经验,区级医院往往承担的是普通孕产妇的分娩工作。”一名三甲产科专科医院产科医生表示。
来自区综合性医院的产科医生华敏(化名)也表示,其所在医院产科尽管没有关闭,但她对自己的职业前景并不乐观,“生育率下降了,我们的业务量也一直在萎缩,病区床位数也减少了一些,划给了其他专科去了。目前,我们也在顺应形势做一些转型,譬如往生殖医学方向发展,但生殖医学的发展也是需要市场需求来支持的。”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名誉院长程蔚蔚也认为,未来产科要做的还有很多,“比如对孕产妇的关爱服务,包括对其心理、睡眠问题以及营养健康的关注,还有产后门诊、新生儿儿保工作的开展等等,只有积极去应对当前产科带来的挑战,才能真正推动这一学科的良性发展。”
作为一名区级综合性医院产科医生,伍颖(化名)看到科室孕产妇分娩量降至高峰期时的1/4。她坦言,“正因为产妇少了,我们有机会‘充电’,在孕产妇管理方面做得更加细致,将‘生的多’转变为‘生的好’。”
在上海,相对于三甲产科专科医院,区综合性医院、区妇幼保健院产科面临的压力更大。即使还没到关闭的地步,一些医院也正经历“产科病床不断缩减”的现实。
“尤其是一些综合性医院,不要完全放弃产科,尽管产科经济效益低,但责任重大,一名孕产妇背后是两条生命,一旦产科萎缩,人才队伍也随之流失,母婴安全保障也将很难实现。”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临床经验的产科医生,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名誉院长程蔚蔚也发出这样的呼吁。
伍颖也有一番期盼。在她看来,其所在的医院产科年龄结构相对较好,大部分医生在30岁上下,“对于我们妇产科低年资医生来说,他们会在妇科和产科之间轮转,今年可能在产科,明年就在妇科,这就意味着产科业务量的减少,对大家的收入影响相对还是少的,同时即使产科医生少了,也能有妇科医生一起参与24小时值班,来保证分娩安全。”
“正是分娩量的下降,可以让我们产科医生有余力、有时间去应对这部分高龄、高危的孕产妇,给予她们更多的关注,从而来确保分娩的安全性。”伍颖进一步表示,过去,产科遇到的孕产妇大多数是普通案例,而现在医生要做的,是努力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的整体提升,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在新生儿抚触、家庭参与、孕妇学校等方方面面给予孕产妇家庭更好的体检。”
相比过去时常加班的忙碌,伍颖如今都能正常上下班,工作也算充实,“病人少了,但对我们的工作要求更为严格了,就单个孕产妇而言,我们付出的工作量其实比以前多得多,管理也更加细致了。”这是伍颖以前从未有过的体验。
对于产科遇冷的现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生育率下降,尤其是在经历了2016年生育高峰之后,全国各地出生人口数量下降趋势明显。2017年至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为1723万人、1523万人、1465万人、1200万人、1062万人、965万人、902万人,数量逐年递减。
“忧愁”之外,也有另一种声音。“产科关闭并非洪水猛兽,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一名三甲专科产科医院负责人认为,当下更要正视现状积极应对,考虑如何把产科做得更强。
在汪栗看来:“一方面是时代在进步,女性地位提升了,对生育有了更多自主选择权,另一方面是科技进步了,如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现,给了不少育龄女性延迟生育的理由。”
伍颖所在的是另一家区综合性医院,“我经历过产科最高峰,一个月生孩子的有400多个,每天都在加班,现在一个月最少时只有七八十个,多的时候也就120多个,差不多只有高峰时期的1/4。”
广发精彩54岁的产科医生汪栗(化名)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末产科的忙碌:一个晚上8个剖腹产,2-3天翻一个班。下班回家洗个澡,睡一觉,醒来马上又要奔赴产房。但就在一年多前,医院的产科悄无声息关闭了。汪栗还记得,产科关闭前,有时一整晚一个剖腹产病人都没有,除夕夜也没有一个新生宝宝诞生。
需要关注的还有产科服务本身的经济特性。一名三甲专科产科医院负责人表示,业务量决定着产科绩效的考核,也决定了产科医生的收入。在国家对医院绩效考核的标准下,产科不涉及高等级的四级手术,这让产科在医院科室考核中不具有优势,“还有很矛盾的一点是,产科要做得好,应该是预防保健做得好,而不应该去考核重点病种,产科与其他科室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把关口前移了。”
那时的汪栗,从没想过医院产科会有关闭的一天。但这些年,她还是看到越来越多的产妇往三甲专科医院挤,区域内的妇幼保健院建卡人数也逐年减少,只能无奈接受这一现实。曾与她一同并肩作战的产科医生们,一部分也开始从事行政工作,还有一部分去了院感科。
“以前,在我们业内有句流行语: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上世纪90年代末,汪栗成为一名产科医生,那时她30多岁,加班成常态,产房里孕妇的叫声此起彼伏,手术一场连一场。身体原因让她不得不从产科转到行政岗位,“是被逼着转型,毕竟作为产科医生,锻炼的机会很多,孕产妇也不愁。”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全国妇产(科)医院数量从2019年的809家下降至2021年的793家,减少了16家。同时,全国妇产(科)医院病床使用率也从2019年的52.24%下降至2021年的44.08%。
这样的担忧,也存在于儿科医生、幼教等诸多群体。正如段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产科的分娩量下降,直接影响到的是儿科,因为孩子少了,儿科的业务也少了,相应的,孕婴童产业,教育培训机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整个教育体系和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伍颖解释,相比20多年前,现在分娩量尽管下降了,但接诊的高危孕产妇多了,“过去,分娩人群中,20多岁女性是主力人群,40岁以上分娩的女性很少,但现在无论是头胎还是二胎,都是30岁以上女性是主力,20多岁的人很少,还有很大一部分是40岁以上的人群,这种变化近五年来特别明显。同时,这些孕产妇在经济条件方面也更好,对于临床服务的需求也显得更为多元化。”
当前,医院产科关闭已不是个例,纵观全国,浙江、广州、福建等地多个省份的医院暂停或取消分娩服务。仅仅一年多来,经媒体公开报道的就已经超过了10家。
汪栗记忆犹新,就在一年多前,医院产科关闭时,有产科医生跑来对她说“我们是跟不上时代的一组”“被人嫌弃的一组”,“特别是一些年龄大了的产科医生,他们的内心是很失落的。”
事实上,中国助产资源还谈不上充裕。据财新周刊援引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截至2020年,中国每万人就有33位护理员和助产人员,分别是芬兰的七分之一、澳大利亚的五分之一、加拿大的三分之一、法国和日本的四分之一。
伍颖有时也会担忧,随着医院产科的萎缩,愿意来做产科医生的人也会越来越少,“作为规培基地,过去我们一届最多招到过4个(规培生),但现在一届只有2个,从2012年成为规培基地至今,我们总共毕业了15名规培生,有2个不做医生,有1个转型做了b超医生。”伍颖说,或许今后招生会越来越难。
一项官方统计解答了女性“不想生”“不肯生”的原因。根据2023年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在上海常住人口中,不打算生育(下一个孩子)的最主要原因为“对现状满意”,占比近半,为41.8%;其次为“抚养成本高、经济负担重”,占比28.5%,“年龄或身体原因”占比13%,其后依次为“其他”“子女无人照料”“希望生活更加轻松自由”“担心工作或个人发展受影响”“缺少合适的入托、入学公共服务”(并列)“其他家庭成员的意见”(并列)。


 换一换
换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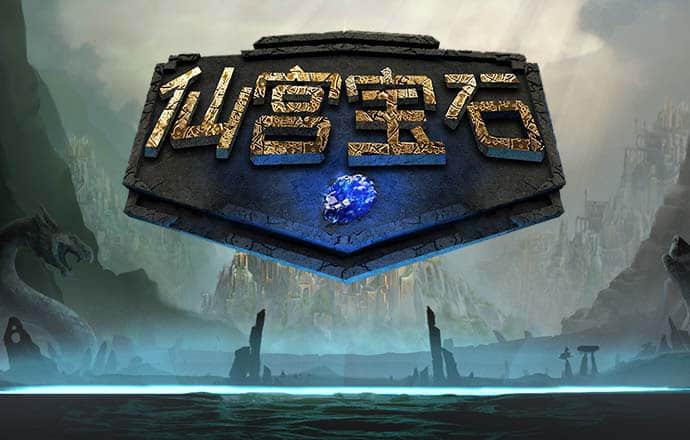

 广发精彩 v2.1.1官方正式版
广发精彩 v2.1.1官方正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