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杜:从我父母的角度,他们只是希望我周游世界,我多多去学习,因为他们是那种非常国际化的人。但是,我自己是想造福百姓,因为我非常实际,不是所有人在喀麦隆甚至在非洲有那么个机会。所以你有机会上学,你有机会出国,你得非常认真、得努力学习然后去造福百姓,去回报社会,甚至帮助我的国家。
门杜随即报名一所当地的孔子学院,从学中文开始,了解这个素未谋面却又“到处可见”的国家。入学六个月后,门杜以全国第一的优异成绩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获得了五级证书。
除了花茂村,门杜还去过山西兴县的沙壕村。2021年7月,包括门杜在内的非洲13国青年在山西兴县沙壕村,深入田间,与村民互动交流,通过体验当“第一书记”等,学习脱贫攻坚等基层治理经验。
喀麦隆位于非洲中西部,西南濒临几内亚湾,经济中农业所占比重较大,工业和基础设施比较薄弱。2013年,门杜结束德国留学生涯,回到喀麦隆。当时,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刚刚提出不久。
门杜:因为当年我在了解甘肃和贵州的时候,我看有一个易地扶贫搬迁,而且刚好那年是做易地扶贫搬迁。所以,我想去看看,我想去了解,因为发展和脱贫攻坚是我的主线。
门杜:我们非洲一直以来还是靠西方媒体去了解世界,但是现在已经有转变了,不一样了,你能够看到当今的中非合作论坛,应该是奇迹,因为现在就是全非洲都来了,所以我们越来越看重中国,那为什么呢?
门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真实的信息可以影响到双方对彼此的理解,这个很重要。因为合作伙伴是个朋友、是个兄弟,你但凡对他有偏见的话,那肯定是合作不来,你可能会往贬义去想,可能你会忽略到他所做出来的贡献。
门杜:我想我主要的职责目前是帮喀麦隆脱贫,摆脱贫困,就像中国那样。我去了那么多的基层乡村,他们现在过上好日子了,包括现在讲美丽乡村,乡村振兴,所以我也是希望喀麦隆也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在北大,门杜一待就是七年,先攻语言,再读硕士、博士。完成学业的同时,门杜经常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结识中国朋友,见证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2017年10月,门杜选择了贵州省遵义市花茂村,作为其探索中国实施脱贫攻坚规划的第一站。
作为非洲青年代表,门杜此次的任务是协助喀麦隆代表团提供相关的服务。从2015年来到中国读书至今,门杜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九年的时间。从当初对中国一无所知甚至有一些误读和误解,今天的门杜已经是一个中国通。他是中非青年联合会联合创始人、非洲青年驻华代表团团长,并荣登“2023年联合国100名全球最具影响力非洲后裔名人榜”。
门杜:当然有帮助,但是谈不了是说要复制粘贴,但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参考意义。因为从中国的视角的话,它有好几个做法,第一,它的对口帮扶,这非常有价值。
记者:因为刚才你一直在讲想看到中国是怎么脱贫,中国的脱贫经验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你把你在中国看到的怎么脱贫,带回去看看对自己国家,或者说对非洲更多国家有没有帮助?
门杜:我去了一共70所基层学校,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当我把真实的非洲跟他们讲,原来非洲也有这个,我说对啊,是有的,他们也会非常乐意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
就算是有现在西方媒体在抹黑,但是我们能够看出结果,我们能够看出、摸得着,从宏观就是一些大项目,亚吉铁路、蒙内铁路、坦赞铁路,甚至在喀麦隆,我们的克里比深水港,已经有非常具体的,我们老百姓能感受到的、能够收获,所以这样的做事风格,再多的媒体肯定也抵不掉。还有我刚刚列出来这些大项目的话,这也是解决了非洲面临的第二大问题,就是今年的就业问题。
门杜:它修得非常快,而且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我们看得着的、摸得着的,包括现在最新的中国在给喀麦隆建一个我们新的议会大厅,很快就要落实,很快就要修好了。所以我就觉得越来越好奇,我想过来中国了解它的根。
花茂村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由于部分村民原来居住的山区不仅偏僻,而且存在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当地的政府对这部分村民实施了易地搬迁。之后,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到了2019年,花茂村实现了整体脱贫。2021年,花茂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1万元,比2012年增加2倍以上,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大乐透试机号9月4日至9月6日,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举行,这几天,生活在北京的喀麦隆小伙门杜也忙碌了起来。9月4日接受《面对面》记者采访时,他刚刚完成对喀麦隆代表团的接待工作。
博士毕业后,门杜并没有马上回国。2023年9月,他加入中非民间商会,担任中非民间商会的国际交流部副主任。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门杜看到了不一样的变化,这些变化验证了他多年的思考,其中也有他的一份贡献。
门杜:没错,自己去体会、去发现真实的情况。借助青年对话,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这么一个方式,再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再包括鼓励比如说中非双方媒体有更加紧密的合作。包括非洲那边的一些媒体人来中国培训,包括中国这边去非洲去交流,因为我还是认为中非双方相关的叙事,必须由双方来写,就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关键词,都不是非洲出的,比如说“债务陷阱”。如果你看在非洲许多国家的债务指数,中国只占一点点,那何来“债务陷阱”一说?所以,像这些个叙事是我们中非双方必须得亲自去写,而不是说第三方给我们界定一些词。


 换一换
换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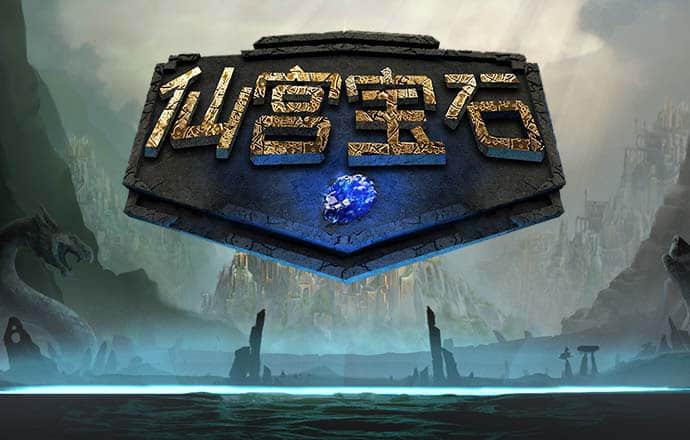


 大乐透试机号 v3.3.7官方正式版
大乐透试机号 v3.3.7官方正式版